可塑的身體與AI年代
曾瑞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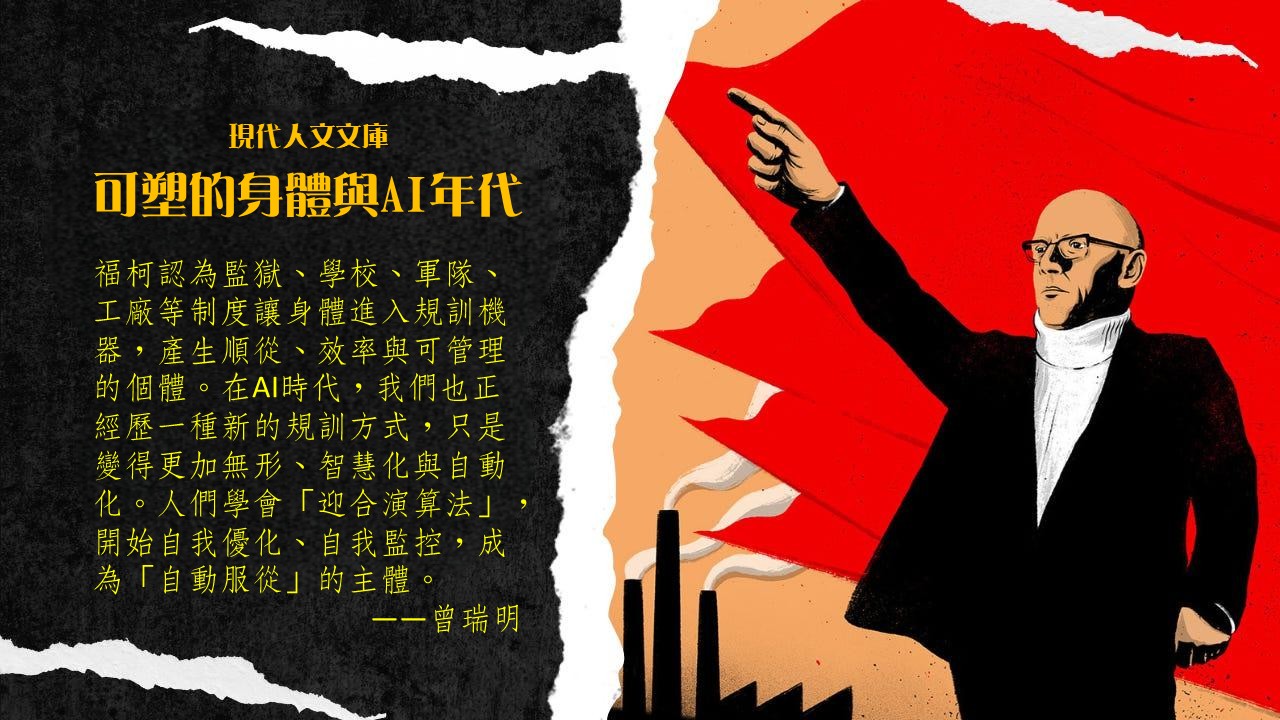
提要:
本文旨在探討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可塑的身體」概念,並將其思想延伸至AI時代。福柯在《監視與懲罰》中指出,紀律技術如何從過去對身體的公開懲罰,轉變為透過微觀、日常的權力機制,將身體塑造成「服從、可控、可生產的個體」。作者認為,這種規訓不再僅限於傳統的監獄、軍隊等場所,而是在AI時代演變為無形、智慧化的「數位規訓」。演算法、健康應用程式與社群媒體等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收集、分析與塑造我們的「數位身體」與行為模式。文章最終引導讀者反思,在技術持續塑造我們的當下,如何保存個體的「真我」與自主性。
關鍵詞:
福柯、《監視與懲罰》、可塑的身體、紀律、權力、AI、數位規訓、演算法
正文:
法國哲學家與歷史學家保羅-米歇爾·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深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影響,用系譜學的方式展示我們對不同事情的了解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塑造,而非一直如此,自有永有。其著名作品包括《監視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976)與《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等。我們在此討論的〈可塑的身體〉(Docile Bodies)一文則是來自《監視與懲罰》一書。《監視與懲罰》就是探討現代刑罰制度歷史的;福柯分析懲罰在社會的作用,亦探討權力關係如何影響懲罰的形式與實踐。
可塑的身體一文的背景正是與懲罰有關。18 世紀的懲罰改革,正是針對過去的刑罰方式,比如車裂、絞刑、鞭打,並以公開的方式對犯人施以極端暴力,懲罰的是身體;但這種做法逐漸被認為野蠻、不文明,故被呼籲廢止。懲罰有了新的目標,就是變成改造犯人的內在世界,包括其思想、行為模式和道德觀,而不再是傷害他的身體,這使身體成為權力作用的載體,任由權力去塑作。「可塑的身體」指的正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東西;像從沒有形狀的黏土中,被建構出所需機械的一具笨拙身體。」
福柯從17世紀的理想士兵形象開始討論,他們的身體與行動都極易辨識。我們不只看他的衣著,也看他的步伐——他們是經過訓練的,而所謂訓練其實已是一系列權力的運作。其實,在古典時代(指的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特定時期,大約從 17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末(約
1650–1800 年),一個哲學與知識體系變革的關鍵時期,福柯用來描述現代性興起前的社會與知識組織方式,已發現了「身體」作為權力的對象,紀律技術早已存在於修道院與軍隊中,但到了17、18世紀,它成為一種普遍的支配公式。一種針對身體的強制性政策逐漸形成,人的身體進入了一個對其重新排列與操作的機械中。這象徵了政治解剖學與權力機械學的誕生。
「馴服的身體」成為可以被支配、使用、改造與提升的對象,它最初只是一塊「無形的黏土」(formless clay),缺乏任何預先設定的身體姿勢、動作規範或時間節奏。它既不夠「服從」(obedient),也不夠「有用」(useful)。18世紀的紀律項則揭示了控制的新規模。身體的經濟性開始受到重視,而控制的方式是一種持續、不間斷的強制力量,它依據某種時間與空間的編碼運作。這些方式就是「紀律」(disciplines),也就是控制身體操作的技術,形成一種馴服與效用之間的關係。
控制身體成了一門學問,「政治解剖學」主張權力可以深入到最微細的身體層面,例如行走方式、坐姿、用餐方式、學習順序、工作節奏等。權力機械學則是指一種細膩、計算化、規劃性的權力操作系統,像一台機器一樣有效率地作用在身體上,使人們成為「服從、可控、可生產的個體」。福柯還指出一種「權力的微觀物理學」,權力如何在細節中運作,如何透過日常制度、規則與行為影響我們的身體與思想。
福柯確實非常重視「小事」(little things)在權力運作中的角色。他認為真正有力的控制,不是透過公開的大型懲罰或暴力來實現的,而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小、反覆、看似無害的細節,這些「小事」組合起來,構成一整套強而有力的紀律機制(disciplinary mechanism)。
紀律後來開始「擴張」,進入整個社會的治理邏輯之中。這時候,它就不只是「地方技術」了,而是一種可以規劃整個人口、空間、行為的國家治理技術。他這樣說︰「思想史學者通常將對於完美社會的夢想歸因於十八世紀的哲學家與法學家;但其實,還存在著一種軍事式的社會夢想:其根本參照的並不是自然狀態,而是像機器中嚴密服從的齒輪;它所依據的,不是原始的社會契約,而是持續性的強制;它關注的,不是基本權利,而是無限延伸的訓練形式;它所追求的,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動的馴服性。」
福柯這樣說其實是指出實然狀態,政治並不是請客食飯,而是監管與服從的延伸而已。但福柯從沒有明確提出一條「解放之道」,但他為我們提供了工具——透過對權力的分析和自我技術的探討,讓我們能夠意識到權力的機制,尋找生活中可行的抵抗與自我轉化方式。
在AI時代,我們的可塑性已不只限於身體,我們的行為、習慣、甚至思想都被數據化、被收集、被分析,最終也被「訓練」與「再製」。健康app、穿戴裝置、社群平台上的行為演算法,其實就是在重新分配與塑造你的「數位身體」。
福柯認為監獄、學校、軍隊、工廠等制度讓身體進入規訓機器,產生順從、效率與可管理的個體。在 AI 時代,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新的規訓方式,只是變得更加無形、智慧化與自動化:演算法就是新的時間與空間規劃表——根據你的喜好推薦內容、限制你的可見範圍,讓你的選擇看似自由,實則被安排。工作自動化與績效追蹤,則讓員工的效率變得「透明」與「可監控」,有如現代的數位監獄。全面評估個體行為的雄心,唯有仰賴 AI 技術的協助,透過各種媒介(社交網路、智慧監控攝影機、連網裝置等)收集數據,將其轉化為資訊(法律及生物識別身份、行為、社會關係網絡等)。在對公民和企業進行道德規範的背景下,此系統可被視為福柯所說的「政治的身體技術」與「權力微物理學」:對身體的監控與管理是改革思想的前奏。人們開始自我優化、自我監控,成為「自動服從」的主體。我們學會「迎合演算法」,塑造自己為可被看見、可被推薦的存在(如社群創作者為了流量調整行為)。
我們可以想像福柯用他的分析方法去分析AI如何塑造我們的內在。但當他沒有提供一條出路時,我們就更感悲觀和失望,我們知道自己如何被塑造,但我仍有真我嗎?如何保存?這就是規範性問題仍重要的理由。
—全文完—
前往現代人文文庫:
http://www.hksh.site/modernhumanities.html
※請前往人文臉書讚好、分享或評論:
https://www.facebook.com/modernhuma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