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行與王守清如何互相影響共同開拓荷花彩墨創作
李冠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社會科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文學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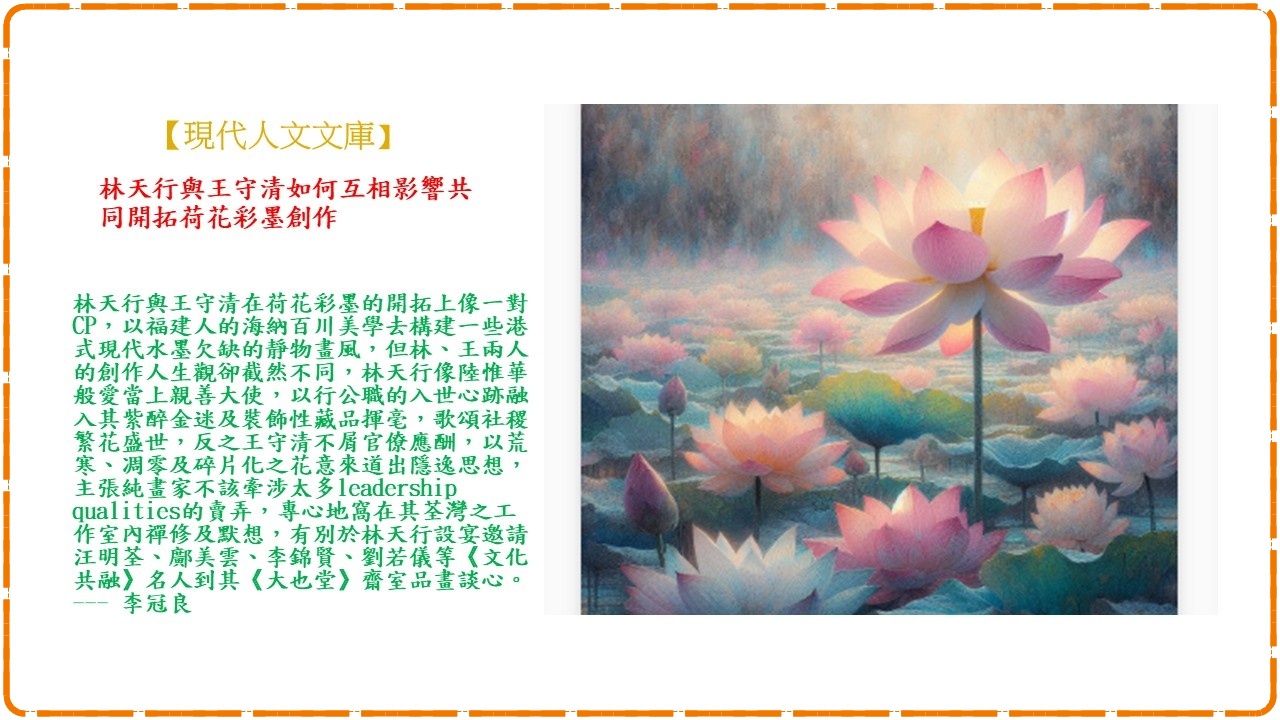
編者案:
本文是李冠良先生的講座《林天行與王守清如何互相影響共同開拓荷花彩墨創作》記錄文稿,文題及所有章題均為編者所訂。
提要:
本文旨在將林天行與王守清這對看似商業化的藝術家,置於「儒家入世」與「道家避世」、「華族中心」與「西方解構」的宏大對立框架中,進行了極具深度的學術闡釋。其論述旁徵博引,見解獨到,生動地展現了當代水墨藝術在傳統與現代、商業與學術、本土與全球之間的複雜張力
關鍵詞:
林天行、王守清、荷花彩墨、色俗、米家墨氣、拙味、臥遊觀、遨遊觀
精華摘錄閱讀:
本文分為以下七章:
一、講座開場與主題介紹
二、藝術家背景與文化差異
三、藝術風格與技法比較
四、外部影響與哲學觀點
五、意境與哲學比較
六、設計文化與成功研發探討
七、市場定位與講座結語
精華摘錄是第一章至第三章內容。
一、講座開場與主題介紹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來到「中西人文講壇」。今天又是我來主講,這次的講題是:「林天行與王守清如何互相影響,共同開拓荷花彩墨創作」。
林天行和王守清這兩位藝術家,你們可能會問,他們的作品是否屬於非常學術化的類型?其實並不算,他們絕對是走商業畫廊路線的藝術家。這與劉國松、呂壽琨或王無邪那些攻學界或博物館的路線完全不同。
然而,林天行和王守清雖然同樣攻商業畫廊和收藏市場,但他們的理念卻有著些許差異。如果他們創作一些作品來標誌百花盛世的景象,那其實屬於一種裝飾性的畫作。這種裝飾性的畫作,有時與墨意的研發並沒有太大關係。
現在,我們試著用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來看,他們兩位到底有什麼不同之處,以及如何互相影響,共同開拓荷花彩墨創作領域。
二、藝術家背景與文化差異
林天行和王守清,他們兩位都是福建人,但背景大不相同。林天行是正宗在內地讀書,修讀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山水畫專業。王守清則留英攻讀現代藝術,畢業於英國倫敦中央藝術學院和英國倫敦溫布頓藝術學院。
林天行堅信領袖才能,王守清則主張「畫廊包養」。其實,林天行是比較正宗的華族中心主義者,他的思維模式都是華族中心主義的。雖然他的表現力或色感有點像林風眠,但他骨子裡是個華族中心主義的人,因為他沒有留過洋,說真的。
但是王守清,那時候他省吃儉用儲了一些錢,拿到獎學金,突然之間衝出中國、衝出香港、走向世界,和蔡仞姿去芝加哥藝術學院做現代藝術一樣,面對一個嶄新世界。蔡仞姿那時候面對安迪・華荷、威廉・德・庫寧、傑克遜・波洛克、漢斯・霍夫曼那個火紅的年代;而王守清就面對法蘭西斯・培根、比利・查爾迪什、查爾斯・湯姆森這個火紅的年代。
王守清面對歐美的文化衝擊思潮,他在民族繪畫方面,那份民族自尊是比較低的。他覺得現代主義那些概念的元素,反而是可以幫到他自強。就變成他不會太過著重那些筆墨秀氣的畫論,最重要是有一種表現力。
好了,兩個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一個比較貼近中國文化一些,貼近中國文化的那個就比較講求領導才能。他主張與貴族和皇權階層的人去交流,因為文人一定是服務上流階層,不是服務弱勢社群的。這是林天行的定位。
他會主張參政,那個參政的理念包括做藝術行政。但是王守清就不喜歡做藝術行政的,王守清不玩Facebook,林天行就很喜歡玩Facebook的。王守清是比較獨行獨斷的,總之他站開一邊去想創作,就不理人了。如果他想生存,就「躺平」去求那些畫廊包養。他會叫人做的,不會自己做的。
那就變成兩個人的經營理念是不同的。一個是真的去很外向地去推銷自己,去聯絡一些贊助人。王守清就比較內斂一些、封閉一些,總之就是躲開一邊。不是說他完全不打電話給那些畫廊或者策展人,但是他又不很高調去應酬或者取悅他們。
林天行積極參加「文化共融」,和香港美協等等的公職。基本上,林天行在內地美院讀中國畫系,他是有一個層級階層的學習模式:學這個素描構圖、學這個白描、接著學這個寫生、學這個墨意幻化,然後再去學創作,然後再去學怎麼去做研究式的作品,就是以研究為本,是有一個層級性的。
但是王守清就是所有規則都應該被解構,就是不會有任何的構圖、造型能力、點線面,去框死了他的想法,而是他很跳脫地去想怎麼去迸發一些激情,或者是將一些的畫面虛無主義化,去「躺平」,去吸引一些當代策展人喜歡。就變成他不是集中在那裡練書法、臨帖,或者是去臨摹一些的仕女圖。
這些背景差異,讓他們在荷花彩墨創作上互相借鑒,林天行的層級性學習影響王守清更注重表現力,而王守清的解構主義則讓林天行在裝飾性上更自由。
1.林天行的華族中心主義與領導定位
林天行的背景根植於傳統中國文化,他強調領導才能和參政,通過藝術行政融入上流階層,這種積極入世態度影響了他的荷花彩墨更注重陽剛氣和行氣表現。
2.王守清的現代主義衝擊與內斂風格
王守清的留英經歷讓他面對歐美文化衝擊,他主張畫廊包養和獨行創作,這種內斂風格在荷花彩墨中體現為表現力和虛無主義,同時也影響林天行在色感上的大膽嘗試。
3.公職參與與博物館進入的比較
林天行積極參與公職如香港美協,而王守清則通過畫廊鞭策進入博物館,這種差異展示了他們互相影響的經營策略,林天行學會更注重品牌,王守清則借鑒領導性來擴大影響。
三、藝術風格與技法比較
林天行積極參加「文化共融」和香港美協的公職。「文化共融」其實是用來參選藝發局和立法會的文化、體育、演藝及出版功能組別的議員席位的。「文化共融」在後國安時代,其實當選的機會是大很多。林天行其實不介意幫忙去參政。
他能夠駕馭著天趣畫廊,他可以叫他們怎樣去擴大理念來做。總之我要博物館級就博物館級,我要「遊子天涯情繫海西」,整個華東地區同鄉歌功頌德的勢力都給他用盡。天趣畫廊給他做得到,這件事我就認為,好像我以前在浸會大學,沒有「上莊」的情況有些相似。
不上莊的人反而可以進入博物館。你們覺得公不公平呢?但是社會現象的確是:林天行有「上莊」,但是他做來做去都是中央圖書館或者是大會堂,所有那些什麼世界級的華人傑出書畫聯展,其實都是在大會堂和中央圖書館舉行,就是循規蹈矩出來的。
但是王守清是沒有「上莊」的,是天馬行空地去進入博物館的造夢國度,進入一個博物館的那種烏托邦的境界。因為福州美術館和廈門美術館都有要過他的作品,那時候火紅得很,是不是?
所以林天行與其見到這個產業結構,是演藝界能夠呼風喚雨的,不如融入這個文化。就變成他與汪明荃和鄺美雲有所溝通。這些人脈差異,讓他們在荷花彩墨的技法上互相借鑒,林天行的陽剛筆法影響王守清的表現力,而王守清的內斂則讓林天行在裝飾性上更注重情感表達。
1.林天行的荷花彩墨技法分析
林天行會用金漆宣紙的背景去畫荷花,彰顯這種「色俗」——「色俗」是俞劍華先生所說的術語,就等於「媚俗」,但是在商業畫廊和收藏家的角度來說不是錯的,或者在描寫繁花盛世方面也不是錯的。因為你沒理由每次都是元代四大家,就是王蒙、或者是倪瓚、吳鎮和黃公望那樣,淡而無味的。還有那個「色俗」也可以供應到酒店的裝飾品收藏市場。
勁挺的筆是對應元代柯九思,寫篆隸書法的中鋒風骨。你看到林天行他拿的那個狼毫是非常有力,還有那種是謝赫六法所說的「骨法用筆」的樣子。其實林林總總那種三宋兩沈的臺閣體的功夫,是做得非常到位,在寫幹用篆法的方面。就是對應一種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那種剛強的性格,還有那些字體是有一種的行氣。連帶畫的那些畫都有一種行氣。
如果不是用篆法去表現那些的橫線,就會好像宋徽宗的「瘦金體」那樣很纖弱。纖弱就不是林天行的風格,因為林天行個人是比較陽剛氣重一點,比較積極入世和樂觀的,就不會說是畏畏縮縮那樣。宋徽宗那些「瘦金體」那種骨法是不對的。
還有他有籀文帖學和方筆的功夫。那個方筆是會有回鋒收縮的,還有那種「堅瘦如柴」的那種乾身的境界,還有那種有一點像刀鋒的境界,那個是方筆。那個籀文帖學其實是比較傾向隸書多一點的,就是小篆和大篆,還有隸書都是。就是籀文帖學是這三種字體比較多一點。有些都會加上金文和鳥蟲文的。
林天行如果畫一些蝴蝶採花的荷花的話,都會有時候學一點鳥蟲篆的筆法,那些的骨法都有的。接著,「拙味」的境界是兌現金石味。那個金石味其實是和清代揚州畫派那種,即是飛白、沙筆那些感覺是差不多的。而且是有一些粗壯得來有一種稚氣的味道,那種叫做「拙味」,不是說很工匠性那種,是有一種粗獷味,粗獷味是有一種陽剛氣的。
《花瓣流露》撞粉法的艷麗幻化味道。那個撞粉法就是他不介意厚塗鈦白,他當作好像林風眠那樣,好像西方油畫那種厚彩厚塗的處理方法是沒有問題的,就不一定要是淡雅的設色分明。管偉邦說畫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如果太厚塗就會好像油畫那樣。但是林天行他畫這個荷花彩墨,就很明顯就像林風眠那樣,真的當他是油畫。
那個鈦白很明顯是重彩的,然後那個洋紅也是重彩的,再拿一些潤筆去幻化。他零零碎碎的,花瓣是重彩的,其他的那些墨色是淡雅的,都沒有什麼所謂的。就變成好像印象派的那些點彩效果,那些點彩的零碎是厚一點的顏料,但是那些線就反而是薄一點的顏料。
所以其實你說是不是那些重彩,就會好像油畫那樣做得不對呢?這個是管偉邦的理論。但是如果你說從林天行的角度去看,又不是不對。因為其實撞粉法是可以真的好像一塊漿那樣,那種的質感的感覺都可以的。沒有說國畫不可以有質感,乾了也有一種質感。
那其他的那些墨色的荷葉,它們吸收在紙上。但是如果你說花那裡不吸收在宣紙上,也都不是等於錯的。因為濃艷的鈦白,反而是引證到它是「出淤泥而不染」,它是在灰暗的荷葉的沼澤環境底下,零零碎碎的綻放異彩的。
2.王守清的荷花彩墨技法分析
我們看何謂「色俗」。俞劍華先生在《國畫研究》中說過:「色俗者,紅綠雜陳,金碧輝煌,只求艷麗,以投富商大賈之好。習青綠山水、工筆花鳥者,多犯此病。」金耀基校長也喜歡他的「色俗」。
金校長是典型的新儒家學者,他也不是太主張畫家過份避世的,因為儒家是主張入世的。儒家也是積極地融入現代化的、精英主義的階級社會,去臣服於上流階層的安排和決策。所以其實金耀基和林天行,他們的領導性和價值觀是契合的。
他們信奉中國文化之餘,也重視領導性和價值觀的。認為儒家文化也是領導性和價值觀的一部分。所以他們的畫,其實如果做到好像王希孟那樣,滿足到翰林圖畫院是沒有問題的;正如李思訓、李昭道,滿足到唐代集賢院書院也沒有問題的。
林天行是「意筆」上面的「色俗」。「意筆」本來就不是「色俗」的,不過如果加了丹青下去,就可以做到工筆青綠山水,或者是黃筌那些工筆花鳥,或者是呂紀那些工筆花鳥,表現「色俗」的效果。
林天行那些枝幹格網的粗線交錯,他會加一些米點皴和雨點皴在那些枝幹上,那就形成一些積點可以呈現的那種韻律效果。然後那些朱磦的荷花就是畫作的視點,就特別地突出了他的主體出來。
其實林天行的一幅畫,他會有不同的視點,而不同的視點散落,就可以令到那些觀者,享受一種「臥遊觀」或者「遨遊觀」,去沿著那些密集交錯的枝幹去看不同的花,它們是否掌握到蜜糖的花蕊,或者是有沒有蝴蝶採花的那種心機,就可以細微地去閱讀不同角度所看到的畫面。
相反的,王守清的荷花彩墨,他是採取一個「情超未象,但見其情」的路線。王守清的畫,其實最初我沒有什麼頭緒,因為它們只有一些色感,我看不到重心是什麼。我會覺得好像那些流體力學的抽象畫作,都是一些沒有意思的色澤幻化的表達。其實沒有意思的都可以是藝術,說真的,不是一定要有故事畫,或者是研究方筆基礎,有意思才叫好畫作的。
他的花瓣就是有沒骨法和撞水法。沒骨法,清代的陳洪綬和虛谷都經常用的。撞水法的方面,就算他畫的鈦白是很重彩,將一大堆水沾到一支潤筆上,然後弄到那些鈦白是半透明的狀態,勾上幾條花蕊莖就賣得出去的了。其實想的東西不需要這麼複雜。
他的畫有一種米家墨氣的境界,就是米芾、米友仁那種大氣磅礴之氣的感覺。他的用意之妙,其實就像東晉顧愷之的「以形寫神」的境界,他只是拿個神韻,而不是「應物象形」那一種。
他的題跋以俗書之粗糙紋跡,題跋似俗書之粗糙紋跡味道。他不介意那些中鋒、側鋒、偏鋒、逆鋒,或者藏鋒,不介意那些章法,像曾灶財、「九龍皇帝」那些的味道,不會介意的。他反而覺得是有一種的「趣」味,因為那種「趣」味是有「拙味」和有稚氣的。
他去畫花,是想有一種孩子氣,那種孩子氣就是他看花的飄零,是很簡單的,其實就當它是很自由奔放的蒲公英那樣去幻化就可以了。其實王守清他一幅畫,他想的經營層面是沒有林天行想的色彩分佈的構圖,想得這麼複雜的。王守清他想得是很簡單的。
比方圓筆、潤筆,渲染出荷花的神韻和意象。那裡說明,王守清其實某程度他都會學小篆、顏真卿那些的藏鋒,因為圓筆其實是藏鋒的章法的用法。就圓筆來講,寫的字就變成了有一種渾厚,和那種兼容並蓄,與世無爭的味道,就是完全不具攻擊性。
—精華摘錄完—
欲閱讀全文,請訂閱香港人文學會Patreon網,或在該網付費瀏覽,連結為: https://www.patreon.com/hk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