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馬克思看斯多亞主義
曾瑞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兼任講師、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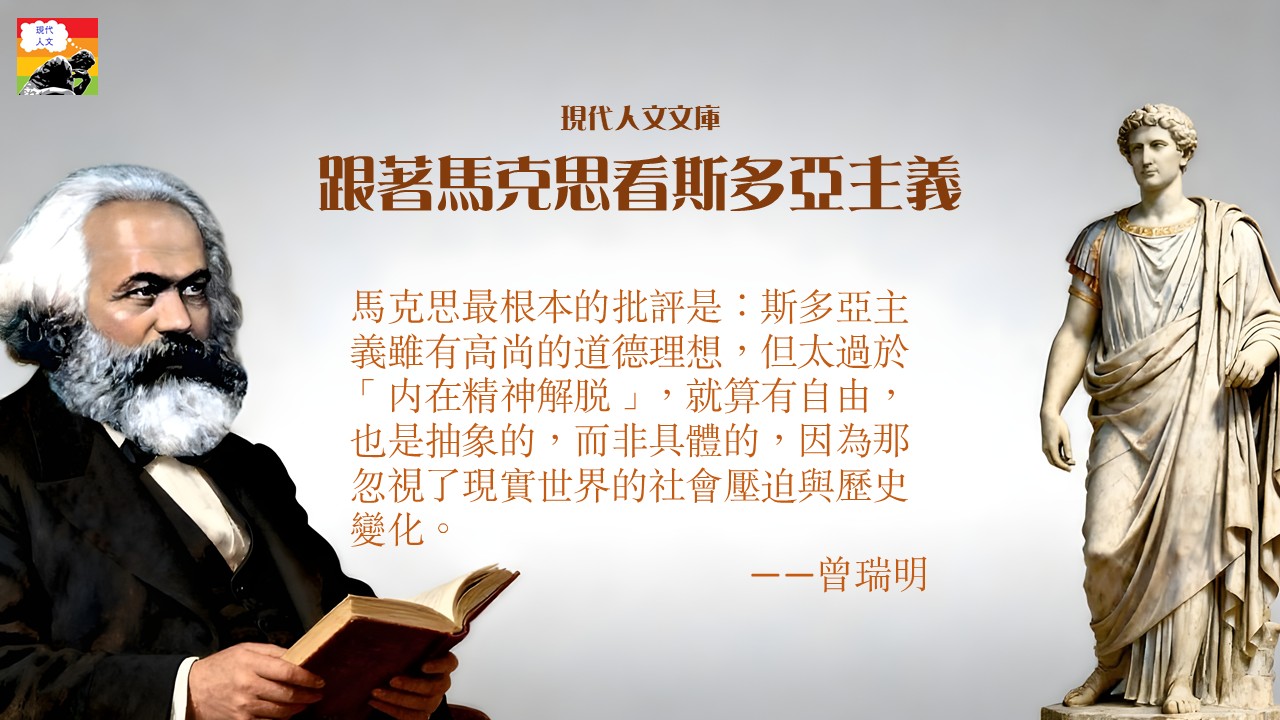
提要:
本文旨在透過卡爾・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別是其《博士論文》,對斯多亞主義提出一種具批判性且超越傳統二元對立的解讀。文章首先從馬克思《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改變世界」的名言切入,呈現其行動哲學與斯多亞主義「順應世界」思想的表面張力。隨後,本文深入分析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對斯多亞主義的評價,揭示其辯證觀點:馬克思一方面批評其自由是被動、抽象的「內在撤退」,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對抗命運的「剛強」精神。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將斯多亞主義、伊壁鳩魯主義與懷疑主義定位為希臘哲學「自我意識」的完整展現,是希臘精神過渡至羅馬精神的重要原型,而非傳統觀點下的衰退。儘管如此,本文最終回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批判,指出斯多亞主義因專注於內在精神解脫,而忽略了改變造成痛苦的社會物質根源。藉此,本文為當代斯多亞主義的復興提供了一個批判性的反思視角。
關鍵詞:
馬克思、斯多亞主義、馬克思博士論文、自由、命運、歷史唯物主義
正文: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第十一條的名言大家應耳熟能詳:「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它。」我們帶著句話看斯多亞主義,應該可以斷定馬克思不喜它那順應世界,接受世間有事情不可控制的思想。但我們若看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卻又有新的發現。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與伊比鳩魯自然哲學的差異》。雖然重點是伊比鳩魯,但他也有討論斯多亞主義與懷疑主義。他說:
「斯多亞學派的人試圖透過理性征服命運,他們的自由是在思想中閉合自我、否定現實……這種自由,是被動的,是抽象的。」馬克思雖然欣賞斯多亞學派那種理性對抗命運的姿態,但也認為那是一種不企圖改變世界的內在撤退。
我們若看到這一段,卻發現他形容斯多亞學派為「剛強」︰
希臘哲學似乎遭遇了一件好的悲劇不應該遇到的事情,那就是一個乏味的結局。希臘哲學的客觀歷史似乎在亞里斯多德這位希臘哲學的馬其頓亞歷山大身上走到了終點,即使是那剛強的斯多亞派,也未能完成斯巴達人在其神廟裡所完成的壯舉——將雅典娜鎖鏈拴住赫拉克勒斯,使她無法逃離。
另一段則指出斯多亞哲學是赫拉克利特關於自然的思辨與犬儒倫理觀的混合︰
伊壁鳩魯派、斯多亞派與懷疑派被視為幾乎不恰當的附加物,與其強大的前提毫無關係。伊壁鳩魯哲學被看作是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與屈拉尼派倫理學的綜合;斯多亞哲學是赫拉克利特關於自然的思辨與犬儒倫理觀的混合,再加上一些亞里斯多德邏輯;最後懷疑主義則被視為面對這些教條主義的必要之惡。這些哲學因此不自覺地與亞歷山大哲學聯繫在一起,被視為一種片面且有傾向性的折衷主義。亞歷山大哲學最終被看成完全是一種誇張和錯亂的狀態——在其中充其量只能認出其意圖的普遍性。
而且,出生、盛開和衰退是非常籠統且模糊的概念,雖然萬物皆可歸納於其中,卻無法藉此真正理解任何事物。衰退本身在生命中即已預示;因此其形態應與生命的形態一樣具體且獨特地被把握。最後,當我們回顧歷史,伊壁鳩魯派、斯多亞派與懷疑派真的是偶發現象嗎?它們不正是羅馬精神的原型,是希臘走向羅馬的形態嗎?其本質不正充滿了鮮明的特質與永恆的強度,令現代世界也必須承認它們擁有完全的精神公民身份嗎?
在馬克思這篇論文,斯多亞主義被看作是希臘哲學後期的一個重要學派,屬於「後亞里斯多德哲學」,是從早期哲學(如赫拉克利特)和倫理(如犬儒學派)汲取養分的綜合體系。斯多亞主義並非單純延續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而是從較早期的自然哲學與蘇格拉底學派的倫理思想中尋找根基。斯多亞主義和伊壁鳩魯學派、懷疑論一起,代表了希臘哲學中「自我意識的完整結構」的不同面向,每一個學派都展現了自我意識中的一個特定存在狀態。這三者合起來形成了希臘哲學結束後,希臘思想向羅馬過渡的重要精神階段。
馬克思的分析提醒我們不能像傳統上認為希臘哲學在亞里斯多德後達到頂峰,隨後進入衰退期,晚期哲學如伊壁鳩魯、斯多亞和懷疑派不應被簡單視為衰落或附屬,而是希臘哲學自我意識的完整展現,並且是希臘走向羅馬的重要精神形態,對後世仍具深遠影響。晚期哲學體系不直接基於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而是回溯到更早的自然哲學(如德謨克利特)和倫理學(如蘇格拉底派)。可以說,斯多亞學派是更能把自然哲學和倫理學結合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過得好就是跟自然規律相配合。當然,能否把社會的制度和約定俗成看成自然規律,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馬克思認為斯多亞主義提供了一種「個人如何在敵對的世界中保有自由」的方式。但他並不推祟它作為一套完整的哲學實踐,尤其在他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中,他對斯多亞主義也有批判。馬克思最根本的批評是:斯多亞主義雖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但太過於「內在精神解脫」,就算有自由,也是抽象的,而非具體的,因為那忽視了現實世界的社會壓迫與歷史變化。馬克思主張關注勞動與物質生產關係,強調階級鬥爭與歷史條件,認為那是可以改變的部份,我們要處理「為何社會製造痛苦」的根源問題。
若有這種觀點看斯多亞主義在今天的復興,我們會有一定程度的戒心,是要我們逆來順受,還是追尋真的德性和平靜?
參考資料
https://marxists.architexturez.net/archive/marx/works/1841/dr-theses/ch01.htm
—全文完—
前往現代人文文庫:
http://www.hksh.site/modernhumanities.html
※請前往人文臉書讚好、分享或評論:
https://www.facebook.com/modernhumanities